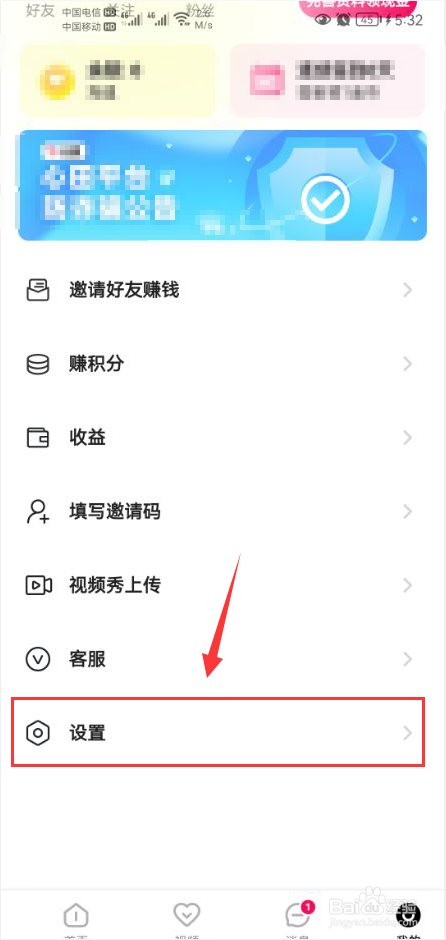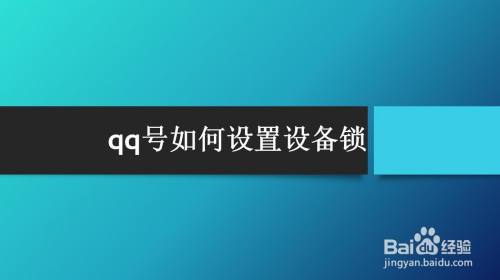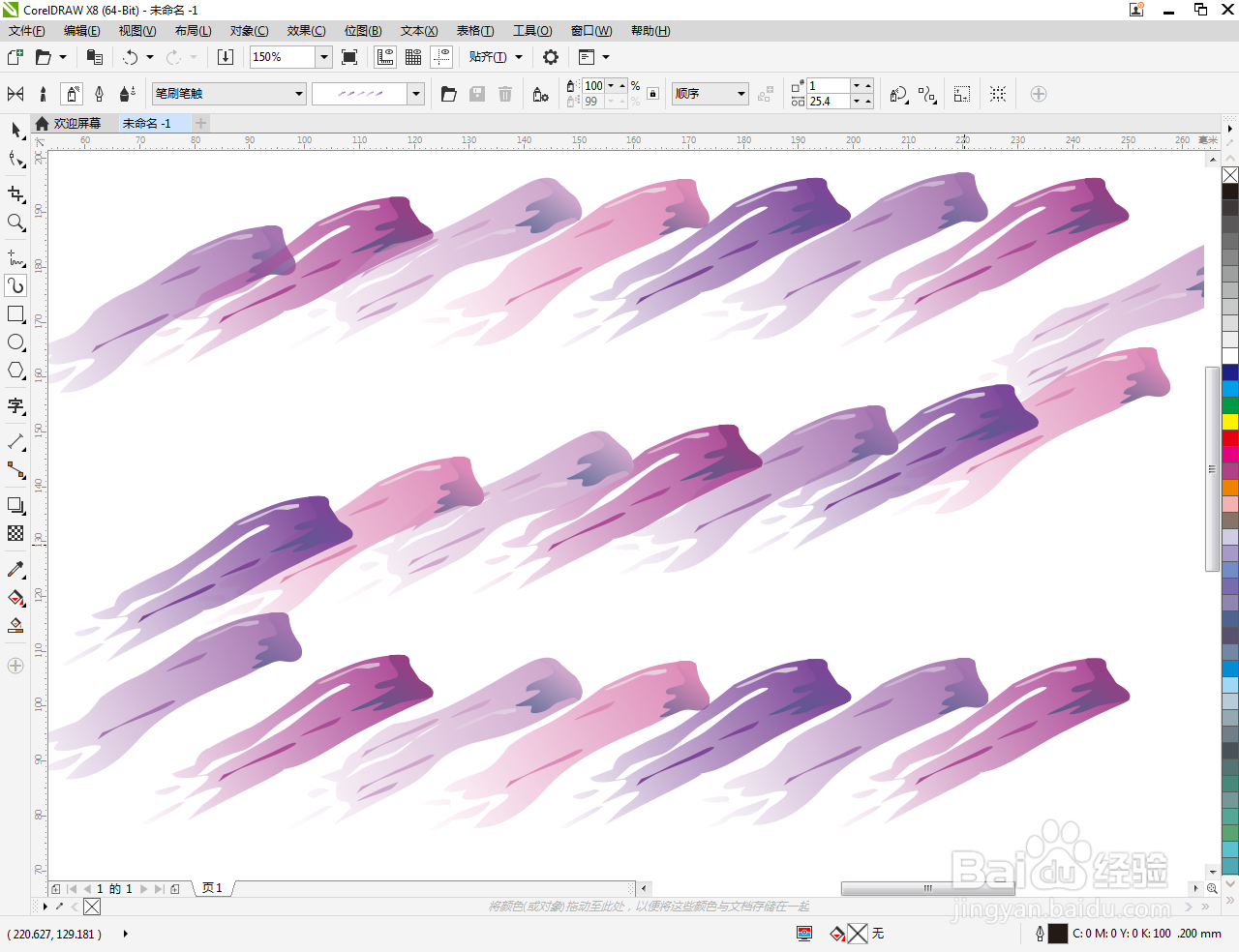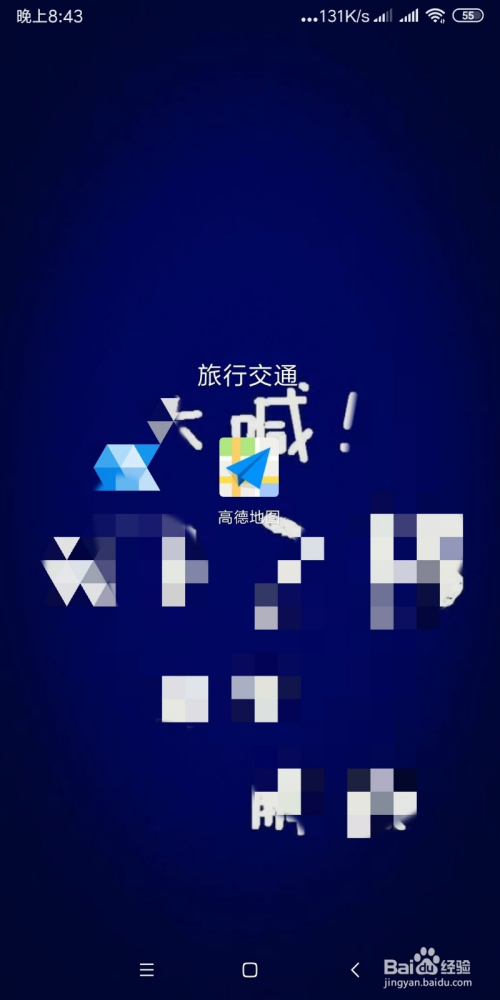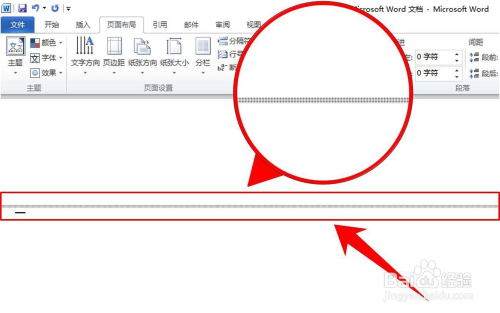鼎新的风险与化解
出于一位带领人的保举,托克维尔的《旧轨制与大革命》(以下简称《旧》)一书在问宿世一百五十多年今后俄然在中国“火”了一把,一时候当作了“人人争读”(凤凰网上用语)的热点书。“书自有其命运”,倒也不足为怪。
坊间对这本书的评介热闹了一阵,至今也还没完全消停。不少文章关心的是这本切磋法国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书“与当下中国的联系关系性”(《人平易近日报》评论文章用语),似乎有揣摩保举者深意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一种读法。“读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终归也是想以史为鉴。惹人注目标是,大大都此类文章都聚焦于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环境是,一贯毫无牢骚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令的人平易近,一旦法令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丢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老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并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当局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凡是就是它起头鼎新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的君本家儿。人们耐烦忍受着磨难,觉得这是不成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本家儿意想消弭磨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那时被消弭的流弊似乎更轻易使人发觉到另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感便更激烈:疾苦简直已经减轻,可是感受却加倍灵敏。封建轨制在盛期并不比行将衰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细的专横行为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轨制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禁锢比路易十四期间龙马队对新教徒的毒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平易近情冲动。
再无人认为一七八零年法国在式微;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前进的限制了。恰是在那时,人能不竭地无限完美的理论发生了。二十年以前,人们对将来无所期望;此刻人们对将来无所害怕。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期近未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们对既得好处无动于衷,同心专心朝着新事物奔去。(210—211页)

一
这段文字论及鼎新可能有激发革命的风险。对于鼎新正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中国”来说,天然轻易触动某种焦炙。有评论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布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期间有某种相似性”(参看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人平易近日报》)。不外我觉得,汗青究竟结果不是在尝试室里进行的,不成反复的身分老是会有良多,“相似性”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概况印象。通读《旧》全书,会觉察托克维尔对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状况做了极为详尽深切且富有洞察力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试图深切到旧轨制的心脏”,并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轨制”。原则上说,我们若是没有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也做过同样深切详尽(洞察力姑且非论)的研究,单凭印象就将之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社会做类比,怕是会掉之轻率。并且,从这样一种类比也很可贵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譬如,若是就此得出中国的鼎新应该缓行甚或止步的结论,显然就很好笑甚而有些可疑。但若是得出的结论是说,鼎新不克不及一蹴而就,需要勇气也需要聪明,还需要谨慎如此,却又不外都是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
引起我们关切的这段文字其实也堪称名言,早已活着界规模内广为传布。我想,之所以广为传布,本家儿要仍是因为此中包含着某种洞见,可以启迪读者心智,而非触动了某种焦炙。静心一读,让我有些不测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这段文字有两个天然段,不克不及笼统论之。两个天然段提醒了法国大革命的两种原因或两重动力,而两者可以说是划一主要。在第一个天然段我们看到,磨难“变得无法忍受了”形当作了一种内驱力,驱迫着人们去抵挡;在第二个天然段我们则看到,还较着存在着一种感召力,呼唤着人们“同心专心朝新事物奔去”。是两种力量叠加在一路才激发了法国大革命。坊间对第一个天然段说得比力多,我此刻则想试着从第二个天然段说起。
一起头我觉得,那种感召力就出自“人能不竭地无限完美的理论”。细心阅读后却发现,那种理论的“发生”其实也首先只是人们受到感召的一种表示罢了。在《论美国的平易近本家儿》一书中,托克维尔也谈到,是平等,唤起美国人发生了人能无限完美这个“与宿世界一样古老”的不雅念。与美国人分歧的是,唤起法国人发生这个古老不雅念的不是平等的事实,而是有关平等以及“非宗教”的思惟(见《旧》书第三篇第一、二章)。阿克顿勋爵认为,是美国的《自力宣言》标的目的法国供给了“将思惟酿成步履的那个火花”,而托克维尔则强调,尽管不克不及否定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可是,那时在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及那时法国思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执行我们作家的设想:他们付与我们脑筋中的胡想以实际的内容”。在十八宿世纪中叶的法国,托克维尔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汗青气象:文人“变为国度的首要政治家”,而他们的思惟竟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处于一种激发态。他所说的“文人”,指的是法国发蒙活动中的著作家们。他从他们有浩繁不合的“政治系统”中归纳综合出一个“最遍及的不雅念”:“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根基的、从理性与天然法中罗致的法例来代替统治今世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所谓十八宿世纪政治哲学,严酷说来,就包含在上述的那个独一不雅念之中。”(175页)继而他又指出:“这样的思惟并不新颖:三千年以来,它不竭地在人类的想象中闪现,但从未固定下来。那么,这回它是怎么占有所有作家的脑筋的呢?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逗留在几个哲学家的脑筋里,却一向深切到公共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乃至关于社会性质的遍及而抽象的理论竟当作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配偶女与农人的想象力都被激倡议来了呢?”于是,“当国平易近终于步履起来时,全数文进修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见《旧》第三篇第一章)。
托克维尔用良多翰墨描述和阐发了那种独特气象,并指出,那样一种由很多偶尔身分和必然身分复合而当作的气象,在法国汗青上也属绝无仅有。读者从中也不难看出,尽管“十八宿世纪政治哲学”至今仍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无论在什么处所,再呈现法国社会昔时的激发态已然是概率极小的事了。明日黄花,风光不再,看来那是特别汗青时刻的特别环境。不外,托克维尔的阐发中有一种洞见却也包含了一种“最遍及的工具”,值得稍加寄望。他指出,那时法国的文人、公众、贵族甚至国务活动家在政治上都表示出某种幼稚立场,原因倒是配合的,即:“因为底子没有政治自由。”他的论断可圈可点:“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此中争论的人,即使不懂国是,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按:指文人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要使本家儿要公平易近们(按:这里指贵族)领会本身面对的危险,正如要使小平易近苍生捍卫本身的权力一样,自由的体系体例都是需要的。”“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轨制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见《旧》第三篇第一章)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对于发蒙抱负激倡议来的“以理性为独一依据,勾勒出极新的蓝图去重建今世社会”的信念,托克维尔固然认为情有可原(旧轨制令人厌倦和绝望),但却持有批判立场。在《旧》一书中他就曾这样写道:“他们觉得,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斯复杂、如斯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平易近而俄然的鼎新。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失落了他们前辈四百年前用那时俭朴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自力自由,谁就是在追求过大的奴役。”(179页)
可以延长一说的是,两百年来,人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此后多次发生的革射中吸收教训,不竭对十八宿世纪法国发蒙思惟及其引起的那种激发态进行了反思。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尤其值得注重的当然是对峙“致力于追求发蒙活动的抱负,但又有所保留”的“自由派”思惟家们的反思。就近可举为例的人是力本家儿“从头发现托克维尔”的雷蒙·阿隆。他认为,当发蒙思惟批判一切崇奉,只认可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崇奉时,就趋于当作为一种陋劣的思惟了。这种陋劣的思惟导致一种陋劣的乐不雅本家儿义立场,他称之为“政治乐不雅本家儿义”。基于这种乐不雅本家儿义,某些“缺乏耐烦的理性本家儿义者”,常常将暴力视为“最后的手段”,时常受到暴力的诱惑,并是以容忍甚或撑持极权政治。不止于此。雷蒙·阿隆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给黑格尔提醒了一个本家儿题:“为理性办事的暴力。”颠末一种汗青哲学的论证,暴力不仅具有了合理性,当作为需要手段,并且,在“汗青必然性”的光照之下,暴力自身几乎具有了价值(想想“文革”中的“阶层斗争”)。我们对那样的论证并不目生。言及此,趁便再多说一点。雷蒙·阿隆说过:“无论是阐述美国或者法国,他(托克维尔)所思虑的都是革命后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社会。”我们或当记住,我们其实也糊口在“革命后社会”之中。从这一点出发去阅读《旧》一书,也许会有另一种收成。
二
回到那段文字的第一个天然段。与习常之见纷歧样,作者托克维尔在这里断言,最激烈的抵挡(革命)往往是在统治者着手鼎新,因而榨取减轻、环境变好的期间发生。这一断言得自一种汗青社会学的不雅察,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活泼的例子。细想一下,我们习常的观点——“哪里有榨取,哪里就有抵挡,榨取越深,抵挡越烈”其实却不是得自不雅察,而是从某种汗青哲学做出的推论。孟德斯鸠就曾辩驳过这种推论:“从上面所说,就仿佛人类的本性将会不竭起来否决专制政体似的。可是固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大都的人们却仍是服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轻易领会的。”还有需要强调一点:托克维尔这里所阐述的鼎新(以路易十六为例),大体上是以改善平易近生为本的。相对而言,一个以加强国力为本的鼎新(例如商鞅变法),方针就不会在于“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鼎新中或鼎新后的政权也往往不会“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维尔的论列。这里的“更好”,当然是以臣平易近的感受为准。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跟着鼎新的进行,臣平易近们对专制弊政的容忍度会日益降低。为什么会降低?一方面是鼎新滞后的弊政会显得加倍扎眼,更主要的一方面则是臣平易近们的“感受却变得加倍灵敏”。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也许会认为臣平易近们太不知好歹,甚至认为人道就是贱,只配接管最残暴的统治。但现实上臣平易近们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视为鼎新的一大当作果,只不外统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晰:原先“人们耐烦地忍刻苦难,觉得这是不成避免的”。那是如何的一种绝望?!可以说,是鼎新让人们意识到磨难并非不成避免,工作完全有可能获得改变,酿成(鼎新者承诺的)另一种样子。是以,容忍度降低表白,臣平易近们对统治者从而也对本身的糊口起头抱有但愿,心智因而才变得活跃起来。有什么鼎新当作就会比臣平易近在精力上的解放更为底子?所以我总感觉,这应该是鼎新者也但愿看到的,至少对于以改善平易近生为本的鼎新者来说是这样。所谓平易近生,从来就不是只包含物质糊口一个方面,“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也不会仅从物质糊口方面着手,除非认定臣平易近如牲畜。
问题却在于,鼎新的进度似乎老是慢于臣平易近容忍度下降的速度,这或许是因为统治者鼎新的意愿老是与臣平易近被唤起的但愿有较大距离?当臣平易近们的容忍度下降到接近零时,革命就不成避免地爆发了。托克维尔于是说道:“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布施持久受榨取的臣平易近的君本家儿。”听上去像是一句感慨,在我看来倒是这段文字中最为要紧的一个论断。风险简直庞大,但当作功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总仍是存在的。托克维尔不是凭空道来,贰心目中显然有实例在。
这个论断的中文译文有可能会引起某种歧义,即:似乎需要有另一个“伟大天才”去拯救想要鼎新的“君本家儿”。我请法文很好的一位伴侣核对过原文,原文中那个“伟大天才”的意思很确凿地是指君本家儿本身的“伟大禀赋”。澄清这点也许并不十分主要,但澄清它却使我得以找到一个佐证——阿克顿勋爵也有一个很相似的论断。他说,古希腊的梭伦就是靠着本身伟大的“政治天才”在雅典完当作了一次“暖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化”。有来由相信,托克维尔也必会赞成把梭伦引为本身论断的一个典范。
梭伦是如何做的?事虽古远,阿克顿做出的一个精辟概述却可帮忙我们得见其荦荦大端。梭伦的鼎新启动于雅典城邦做出的一次选择:“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层所烦扰,为避免暴力录用梭伦点窜法令。”阿克顿说:“这是汗青记录中最令人兴奋的选择。”接下来轮到梭伦做出一系列选择。“经由过程使每一个公平易近都当作为其自身好处的看管者,梭伦让平易近本家儿的身分进入国度。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名誉就是缔造一个公家的当局。’”于是,“依靠赞成的统治代替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倒置了过来”。“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克不及完全信赖,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办事对象的带有警戒性的节制之下。……他将在他看来通俗公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度免于专横统治。他说,平易近本家儿的要义是不从命任何本家儿人而只从命法令。”不难看出,梭伦所完当作的变化(就其深度广度和彻底水平而言)其实已然是一场革命,他当作功避免的只是流血与骚乱。有需要指出,托克维尔但愿避免并认为可以避免的也只是流血与骚乱。雷蒙·阿隆有言:“他(按:指托克维尔)之所以接管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成避免的是平易近本家儿活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并且给自由造当作了尚未愈合的危险。”
从今天看曩昔,梭伦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招巧计。他所做的,不就是我们这里自上宿世纪七十年月末便频频申诉的增强平易近本家儿与法制,或者说以法治代替人治?或许值得一说的是,在梭伦那边,鼎新的方针同时也当作为推进鼎新的本家儿要手段,即便在“维稳”一事上也是如斯:“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否决政治骚乱的独一方式,就是权力的集中。梭伦则起头以分离权力的体例来达到不异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这一点,使他的鼎新得以进入了良性轮回?
梭伦是以伟大立法者的不朽声名载入史册的,他是人类法治传统的奠定人之一。若是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夜,人类回复这种古老传统的尽力尚起步不久(路易十六就未必完全认同),时至今日则早已当作为宿世界潮水。人类在推进法治方面确已堆集了良多当作熟的经验可资借鉴。是以,要完当作梭伦式的鼎新,已不必依靠梭伦式的“天才”人物。现现在鼎新所需的聪明,似更多地表现在以完美法制为本家儿的“顶层设计”上。梭伦鼎新也许还像是一个传说,但近现代完当作的“暖和的、不流血与和平的变化”已不算罕有。
附记:这篇札记涉及的本家儿要册本有:《旧轨制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托克维尔与平易近本家儿精力》(〔法〕雷蒙·阿隆、〔美〕丹尼尔·贝尔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二零零八年版);阿克顿勋爵统一著作的两个分歧中译本:《自由史论》(〔英〕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译林出书社二零零一年版)和《自由的汗青》(〔英〕阿克顿著,王天威等译,贵州人平易近出书社二零零一年版)。其他还涉及《论美国的平易近本家儿》、《常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回忆录》以及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等。为避免繁杂,只对出自《旧轨制与大革命》的引文注明出处。
作者:朱正琳
来历:《念书》